编者按
性灵思想的兴起,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认知。性灵指人的心灵,主要包含才、情两端。阳明心学高扬人的先天良知良能,是性灵说的思想底蕴,强调个体的人的才智与性情,突出个体生命、日常生活的意义,以审美的态度,发现庸常生活中的美。明中后期的焦竑、汤显祖、公安三袁、钟惺、谭元春,清中期的吴雷发、袁枚、赵翼、张问陶等,一脉相承。性灵思想不但在传统的诗文创作中激流涌动,而且在正统文学之外的戏曲和小说中也多有表现。沈复《浮生六记》写琐屑的日常生活,化庸常为神奇,描写夫妇之爱,表达对生活的热爱,正是人的觉醒的表征;徘徊于主流体制边缘、以布衣终老的朴实学者梅鼎祚创作《玉合记》传奇,抒写男女情爱,彰显人之觉醒的社会真相。发现生活,正是对人的发现,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敬畏,客观上与封建社会规范相对抗。明清性灵思潮,遂开启了一个思想的新时代,因之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起源。(雷恩海)
作者:姜朝晖(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教授)
沈复《浮生六记》,以灵动的笔墨,简洁雅训之文辞,描述其伉俪深情、闲情逸趣、山川游历以及坎坷人生,遂使其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展露出一片灵光,感动激发人意,获致美的享受。此乃性灵主义思潮鼓荡之下,对男女之情、庸常生活的审美,预示着近代新思潮的到来、人的自觉精神之彰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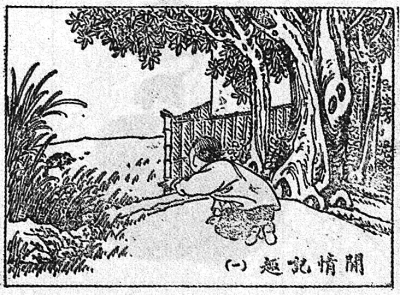
广益书局本《浮生六记》绘图 资料图片
生活于乾隆、嘉庆时期的沈复,仕宦不显,功名未立,当时也并无擅长文章之声名,然而,沈复以审美的生活态度,处于琐屑生活,却能随时发现并欣赏美。
沈复幼小之时,即有“物外之趣”,能够以审美的态度发现美:“夏蚊成雷,私拟作群鹤舞空。心之所向,则或千或百,果然鹤也……又留蚊于素帐中,徐喷以烟,使其冲烟飞鸣,作青云白鹤观,果如鹤唳云端,怡然称快。”这正是李卓吾的“童心”。沈复始终葆有这一童真之心、审美态度,不为生活的粗粝所磨灭。沈复爱花成癖,喜作盆景,精剪枝养节、接花叠石之法,一有闲暇,沈复便巧构花树、盆景,遂使胸中丘壑,化为眼前景致,摇曳生姿,增添一抹亮色,美化生活,高情雅趣。其实,审美生活,并非物质丰盈乃至于奢靡,而往往因陋就简,以雅洁闲适为美。夏月荷花初开,晚含而晓放,妻陈芸“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”。超越狭隘物欲,随顺造化,处处是美。
《浮生六记》最为人所感动者,乃是沈复与陈芸伉俪之情义深笃。对男女情爱的直接表露,是性灵思潮与人之觉醒之重要表征。陈芸,一个有才情而生性洒脱的女子,在琐屑的世俗生活中,两情相悦,于坎坷艰难中,精神相通,情爱相依,支撑扶养之义深淳朴厚。世俗的庸常琐屑生活,两情相悦,不仅仅是耳鬓厮磨之胶腻、依附,而要能交流,有爱好,甚至于有事业可为。既能有相当的一致性,也能有各自的思想与差异性。陈芸堪称闺中良友,与沈复一样爱好书画、叠石为盆景,“至深秋,茑萝蔓延满山,如藤萝之悬石壁,花开正红色,白萍亦透水大放,红白相间。神游其中,如登蓬岛”,神游天地之外,心灵极其自由。
世俗而琐屑的物质世界乃生活之土壤,但也需要有浪漫、高尚的精神,化庸常为神奇。灵明的绽放、艺术的熏陶,是升华精神生活的媒介,是家庭的黏合剂,互相激发,也会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吸引力,起到亲密凝聚的作用。陈芸极珍惜破书残画,终日琐琐,不惮烦倦,分类收集,补缀成幅,而有“断简残编”“弃余集赏”之名,“于破笥烂卷中,偶获片纸可观者,如得异宝”,赏玩不已。课书论古、品月评花,沈复识见不凡,而陈芸亦领悟独到,精神相通遂欢畅自然耳。
在沈复的时代,女子外出游历受礼法的限制,为社会道德所不许。而沈复与陈芸寻找机缘,踏访美景,观赏、游历,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。如,七夕临河赏月,河中波光如练,飞云过天,变态万状,而有“宇宙之大,同此一月,不知今日世间,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”之感慨,正与苏轼承天寺夜游“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”(《记承天诗夜游》)之情趣相仿佛。游太湖,“渐见风帆沙鸟,水天一色”,境界阔大,摇曳生姿。约邀二三知友,踏访苏州南园,陈芸巧为筹划,煮茶暖酒烹肴,对花小饮,得尽其乐:“风和日丽,遍地黄金,青衫红袖,越阡度陌,蝶蜂乱飞,令人不饮自醉。”这样的生活与情味,正是孔门高弟曾皙的理想生活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越陌度阡、游历踏访,离开狭小的圈子,暂时摆脱琐屑的世俗生活,而求得精神的自由与放纵,正是对正常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儒家所讲的孔颜乐处,也就是由审美生活态度而激发,是健康向上的快乐。生活本身就是目的,生活是核心,而快乐则融于日常行为之中,这是性灵思想对庸常生活的意义。腐乳小菜,清茗美酒,或夫妇对饮,或友朋相聚,俭朴的生活,却也充溢着世俗的欢快与精神的高雅。苏轼说:“红日当窗近午时,肚中虚实自家知。人生一饱原难事,况有茵陈酒满卮。”在枯寂、匮乏、甚或窒息的环境中,一杯美酒便突现生活的美好、人生的快意,实乃化庸常为神奇的审美生活态度使然。
沈复喜游历,见识不凡,“凡事喜独出己见,不屑随人是非”。沈复擅长绘画,往往以画家的眼界来观赏胜景,以牢笼天地的本领,用诗意化的描写,将千里之势纳于尺幅之上。游西湖,“觉西湖如镜,杭城如丸,钱塘江如带,极目可数百里”;游西山,“但见木犀香里,一路霜林,月下长空,万籁俱寂。星灿弹《梅花三弄》,飘飘欲仙。忆香亦兴发,袖出铁笛,呜呜而吹之”。苏轼夜游赤壁,“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(《赤壁赋》),享受清风明月、湖光山色,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之雅兴情致,何其相似!武昌黄鹤楼,“冒雪登焉,俯视长空,琼花飞舞,摇指银山玉树,恍如身在瑶台。江中往来小艇,纵横掀播,如浪卷残叶,名利之心至此一冷”,大手笔勾勒,描摹胜景之神韵,读之如临其境。纵情山水形胜,实乃摆脱现实生活压迫、追求精神自由的体现。嘉庆十三年,沈复随御使远赴琉球,册封国王,得以纵游海外,领略异域风光:“瀛海曾乘汉使槎,中山风土纪皇华。春云偶住留痕室,夜半涛声听煮茶。”(管贻萼《长洲沈处士三白以〈浮生六记〉见示分赋六绝句》)。
俗话说,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。艰辛、不易,往往成为生活的底色;历经艰难,甚至成为生活的必需过程。沈复与芸娘并非始终沉浸在美好、快意的生活之中,事实上他们经历了人生的诸多坎坷艰难。《浮生六记》的闺房之乐、闲情之趣、浪游之快以及游历中山,事实上都是以“坎坷记愁”为底色的。沈复为生计而游幕三十年,饱尝流离之苦,生活困窘;伉俪情笃,浪漫性情,超轶当时社会道德规范,为礼法之士所疾忌,又因言语不慎、为弟借贷担保,遂不见容于家庭,被父逐出;两年后虽蒙谅解,得以回家,却又因盟妓、替友作保借贷西人而再次被逐。此后,沈复携病妇寄居无锡,谋食扬州,辗转流离而芸娘亡故,备尝艰辛酸楚。回乡探望,仍不见容;复至扬州,卖画度日,形单影只,凄凉已极。父亡,奔丧归家,而弟贪占家产,百般欺凌,沈复不争纤毫,为友人所援引,寄居佛寺。嘉庆十年(1805),受石韫玉之聘入幕,奔走于荆州、潼关道上,转至山东,骇悉儿子夭亡,其悲痛何如也,“扰扰攘攘,又不知梦醒何时耳”。
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,他们努力追求生活的雅化与品位,精神相通、情爱相依,甚至将审美的愉悦上升到志意之乐,化庸常为神奇。沈复与芸娘“一生坦直,胸无秽念”,俭朴生活,甘之如饴。正是在这种艰辛、不易抑或庸常、无奈的生活环境中,保持一己之性灵,化庸常为神奇,由物质的欲求发展到对精神完善的追求,是人格的升华,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觉醒,是人之为人的开始,也是人性的发现。《浮生六记》彰显出性灵思想的异彩。
性灵思想,能够化庸常为神奇。其一,需要直面世俗生活,认识到世界与生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,能够以审美的心态,发现残缺之中的美、发现阴霾中的光明和亮色。芸娘并非十全十美之人,“两齿微露,似非佳相”,然而聪慧,知书达礼,其才情与文化修养,使其自有一种天生的风韵。其二,真诚,不失赤子之心。沈复、芸娘始终以真诚之心待人接物,不怨天尤人,所谓仁者不忧、君子坦荡荡。因真诚,才能发现并欣赏世俗生活中的美好。其三,尊重与自尊乃美好生活的要素之一,亦是性灵相通、人格平等的体现。两情之相得,重在于有共同的审美、相互的精神交流,要能互相尊重且自尊,而非丧失自我式的依违与攀附。尊重就是承认其独立的人格,自尊乃有所守,而保持自我的尊严。作为闺中良友,陈芸保持着相当的人格独立性,她描述人生理想:“君画我绣,以为持酒之需。布衣菜饭,可乐终身。”其四,要有为,不苟且。世俗生活,需要有所为,保持一点艺术爱好,乃超越庸常生活、升华精神的良方。汲取知识的力量,正是化庸常为神奇、不俗之良方。寄居菜园,赁老妪之室,“四壁糊以白纸,顿觉改观”;而萧爽楼中“四忌”“四取”,更是摆脱庸俗而追求精神之超越与快乐。其五,需要有应对世俗生活的能力。生而为人,离不了日常的琐屑生活,要有一种谋生的技能,能够应对自如。事实上,沈复是比较缺乏这种生活能力的,养成了对大家庭生活的依赖,一旦离开大家庭的庇护,很快就陷入艰难;儿女未抚养成人,女儿当童养媳、儿子入店作学徒,芸娘病重而殁,没有尽到一个父亲、丈夫的职责。
《浮生六记》所展现的,正是性灵思潮鼓荡下的人之觉醒,激发了对琐屑生活的热爱,身处庸常生活而以审美的心态,化庸常为神奇。


